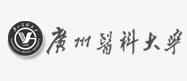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规定,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干股型受贿呈现出期权化、市场化和多样化等特点,越来越具隐蔽性,给监察调查实践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罪与非罪的认定难点。《意见》规定,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按实际获利认定受贿数额。实践中,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是“空壳公司”股份时,如何认定“股份价值”直接涉及罪与非罪。如,某公司虚假出资,或在注册登记后抽逃出资,无真实经营活动,公司股份无现实资金或财产性利益为依托,且从未分红,实际为“空壳公司”。这种情形下,股份价值真实性缺失,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这样的干股能否成立受贿罪存疑。另一种认定难点如,借“空壳公司”收受“约定干股”。行受贿双方为规避调查,事先约定注册成立“空壳公司”,让所送干股无股份价值,待受贿人需要钱款时,如约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或转岗后,再将约定干股由“空”变“实”,按注册资本对应股比兑现股份价值,实现贿赂目的。该情形下,若案发时尚未兑现股份价值,则对认定受贿造成较大干扰。
如何认定上述情形的罪与非罪?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干股型受贿的股份价值必须以实际的财产性利益为依托,因此收受“空壳公司”股份,不宜认定为受贿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的受贿对象是干股对应的钱财,该干股无价值属于其意志以外因素,应认定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可以视收受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接受行为区别认定。对于借“空壳公司”收受“约定干股”情形,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受贿对象是干股对应的财产性利益,客观上如有找人代持等行为,则可以认定受贿,将来受贿结果是否实现则属于犯罪形态问题。对于其他收受“空壳公司”股份的情形,如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时确实不知道该干股为“空壳公司”股份,主观上认为该股份有对应价值,客观上有积极接受该干股的行为,则可以认定受贿;其后股份价值无法实现,属于对象不能的认识错误,影响的是犯罪形态的认定。但是,当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观上不具备犯意或者客观上收受干股行为不明确时,则不宜认定为受贿。如,有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已事先知道该干股系“空壳公司”股份,也知道行贿人并非真想送他财物,但出于感情等其他非财产性利益原因仍为行贿人提供帮助,则不宜认定为受贿。
既遂或未遂的认定难点。股权是否实际转让,是认定干股型受贿犯罪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实践中的认定难点,尤其是“股权代持”型受贿,认定为既遂还是未遂?笔者认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关键,在于收受干股的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干股是否具有控制力。可分两种不同情形。
一是已进行股权转让登记,但由他人代持。有观点认为因受贿人未实际持有股份,所以定未遂。但笔者认为,应视代持人身份以区别判断控制力。若代持人系受贿方的特定关系人或其指定的人,则视为受贿人有足够控制力,可以认定既遂。若代持人系行贿方,或行贿方指定的人,其最终能否实现股权价值尚处于不确定之中,客观上受贿人对干股的控制权存疑,此时如有分红、转让或兑现等控制行为,可认定既遂;但若只有“转让登记”等收受干股的着手实施行为,则属于受贿未遂。二是未进行股权转让登记,以口头或书面协议由他人代持。笔者认为,认定的关键也是看国家工作人员对所收干股的控制力。若代持人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或指定人,所收干股明确有实际股份价值,并有实际使用、转让等控制行为,则可以认定为既遂,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协议形式不影响认定。若代持人系行贿方或其指定的人,有口头或书面协议代持,并明确干股数额,属于受贿犯罪的着手实施,如有转让等控制行为,可以认定既遂。但如果只是口头约定,也没有明确送予的干股数额,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对干股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则不宜认定为受贿。
“干股型受贿”与“代为出资”的认定难点。行受贿双方以合作名义成立公司,约定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占股比例,并由行贿人代为出资,其后公司实际成立经营。该情形应认定为“干股型受贿”,还是“代为出资”?笔者认为,若以“代为出资”认定,在认缴制的注册资本制度下,行贿人可能未实际出资到位或抽逃出资,容易给行受贿双方留下规避调查的空间。若转换思路以“干股型受贿”认定,当证据足以证明国家工作人员未出资而登记受让或实际获得股份时,即可以受贿论处。(陈剑玲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委)